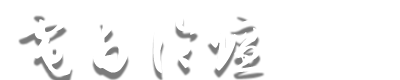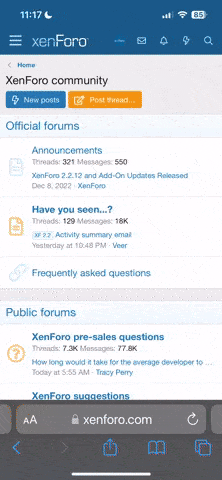捌零後的痛
大学四年级
- 注册
- 2016-10-26
- 帖子
- 948
- 反馈评分
- 177
- 点数
- 41
- 性别
- 男
-
Android Chrome Mobile 142.0.0.0
- #1
尘途琐记
二零零六年,意大利人将那尊铜铸的大力神杯抱在怀里的次日,我立在南京站的风里,与相交数月的女子挥了挥手。无半分戚戚,亦无片缕惜别,只觉风裹着尘沙,扑在脸上,凉得有些茫然。列车的鸣笛声扯得老长,像极了困兽的呜咽,我扒着车窗,看窗外的景物一帧帧向后退,如同我那尚未铺展便已被钉死的前路——家里捎来话,叫我回电白报到,穿上那身素色的教师衣裳,从此困在一方讲台前。这份“前程”,于我而言,无半分欢喜,只余满心的混沌,像蒙了层灰的镜子,照不见半点亮光。
老辈人的心思,大抵是刻在骨头上的:族要立住脚,总得有人往外闯,挣一份前程;也总得有人守着老宅,续一份烟火。父亲早已在外头奔波,留了叔叔在家侍奉祖父母,他怕我在外头成了无依无凭的“无鼻牛”,东碰西撞,终是一场空,便替我选了师范的路子。我那时竟也应得爽快,只因听几位师兄嚼舌根,说师范里头,尤其文科,一个班里几十号人,男子不过三五个,端的是“肉少狼多”,便是一月换一个女子相伴,待到毕业,也未必能轮遍。这般荒唐的念头,竟成了我当时欣然应下的由头。大学四年,兜里侥幸有几个闲钱,便也浑浑噩噩,算得“潇洒”了一场,如今想来,不过是少年人的虚妄罢了。
虽应了家里的安排,可前路于我,依旧是雾里看花,茫茫然辨不清方向。归了家,从教局报到到学校上岗,竟如提线木偶一般,被人牵着走,说不上情愿,也说不上不情愿,欢喜二字,更是无从谈起——仿佛这身子不是自己的,只是按着力道,做该做的事。
到校报到那日,教办的屋子里挤着十五个同来的人,我是最后一个被领走的。来接我的校长,浑身酒气熏人,双眼朦胧,似是还浸在醉意里,含糊问了几句我的来历,便摆了摆手:“搭我的摩托回校?”我摇头:“不必,不如我用小车送您?”他猛地睁了睁眼,错愕片刻,而后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:“刚当老师的,薪水薄得很,你那工钱,怕是不够给车加油。学校地址认得?你先去,我随后就到。”我应了声,便驱车先去了。
我该是镇上第一个开着小车去教书的新先生,自然引来了不少目光。有含着羡慕的,眼睛亮得像要沾点光;有揣着怀疑的,眉头皱着,猜我是来混日子的;还有等着看笑话的,嘴角挂着冷笑,盼着我摔个跟头。世人的心思,大抵是这般,见不得异于常人的,总要揣度几分,议论几句。
归了学校,没等多久,校长也晃悠悠来了,召了众老师开会,无非是把我这个“新丁”推出来,说几句场面话,便引我去看宿舍——竟是一间旧教室劈成两半,里头空荡荡的,只有前后两扇窗,和一扇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木门,风一吹,便“吱呀”作响,像在哭。这宿舍,我四年里竟未住过一宿,只摆了一张竹椅,闲时蜷在上面歇片刻,倒也清净。只是那份薪水,果然如校长所言,薄得可怜,当真不够给车加油,想来也是可笑。
八月三十一日的早会,迟来的课程表终是递到了我手上——五(二)班的语文,兼着班主任。散了会,校长便唤我:“你有车,去把书本作业本拉回来。”我应了,心里却没什么波澜。九月一日,第一堂课,我没发书本,只和三十几个孩子坐着说话,你一言,我一语,光阴竟也溜得快。第二堂课,依旧没发书,我在讲台上扯着自己那些荒唐的“风光事”,台下哄笑一片。这些不过是哄着孩子们欢喜,也哄着自己欢喜。先前有前辈告诫我,这班是全镇倒数第一,调皮捣蛋的多,还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是混江湖的,叫我当心些。我倒觉得,倒数第一也好,没什么指望,便也没什么压力。第三堂课,才慢悠悠把书本发下去。人生大抵是没什么意外的,期末考下来,依旧是倒数第一。只是这一学期,倒也清净,孩子们打架的少了,家长的投诉也稀了,大抵是我这般“不务正业”的先生,反倒合了他们的性子。
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学校这方寸之地,竟也不例外。二十三个老师,硬生生分成了几派:校长与出纳是一伙,攥着些细碎的权柄;主任又是一派,暗里较着劲;还有些官太太,仗着家里男人的名头,也自成一派——这学校离墟镇近,官太太也多。我呢,踩着钟点上课,无课便回了家,不攀附,不掺和,倒也成了独一份的“派系”。正因这般,那些校长里短的八卦,便总往我耳朵里钻,听得最多的,莫过于校长的那些风流韵事,荒唐得很。
在校长和主任眼里,我大抵是个来体验生活的公子哥,瞧不上,也懒得真管。那些官太太,却也把我当成公子哥,隔三差五便来做媒,拉着我见了两三个女子,我皆是落荒而逃——并非她们不堪,只是瞧着那般刻意的模样,只觉无趣。后来再有人来说媒,我一概回绝,倒也暗暗疑心,她们的审美,怕是被世俗磨得走了样。我素来只在上课时分现身,这般“鹤立鸡群”,自然引来了不少关注。许是校长瞧我不顺眼,许是有人在背后嚼舌根,每次开会,总免不了点我的名,说几句批评的话。我听着,只当是耳旁风,依旧我行我素——横竖我没害人,也没误事,何苦要顺着旁人的心思活?
次年,她来了。她这一来,倒把我原本死水般的日子,搅得浑了。她是我大一的第一个女子,也是大学四年里,相伴最久的一个。先前平静分手,闲来无事,只在QQ上聊几句,吐吐各自的苦水,谁知吐着吐着,竟出了岔子。人呐,大抵是逃不过“犯贱”二字的。这傻丫头,竟悄无声息辞了职,不顾家里的反对,一路南下,说是来“讨债”——讨我当年的亏欠。家里人自始至终,都盼着我找个有单位的女子,安安稳稳过一辈子,可那些有单位、模样稍周正些的,偏生瞧不上我们这些穷教师。她能让我那素来反对的父母松口,大抵是因祖父生病时,她守在床前,悉心照料了两个月,这份情分,老辈人是认的。旁人皆是工作爱情双丰收,我却因她的到来,过得捉襟见肘——既已工作,再向家里要钱,总觉难堪,又添上那时爱赌的毛病,日子愈发窘迫,外出闯荡的念头,也便在心里生了根。
二零零七年,我成了亲。父亲竟破天荒从他的公司里,分了些股份和分红给我,说是补偿我留下来守着家里的辛苦。他还唤来两个弟弟,叮嘱道:“日后无论你们谁接手公司,谁另起炉灶,都要分他一份股份分红。我老了,总要回乡下养老,到时候,便靠他照料我和你母亲。”弟弟们应得爽快,想来也是默认了这份安排——我守着家,他们在外闯,各取所需罢了。
二零零八年,倒是不平常的一年。薪水涨到了八百多块,算得一份微末的平静;可股市里,牛市转眼变熊市,五千二百多点直直跌到一千八百多点,先前赚的那些钱,亏得干干净净,反倒欠下二十几万的外债。偏生这年,大儿子也来了,哭声震天,却驱不散我心头的愁云。那时的我,愁绪比胡须还长,望着屋顶的梁,只觉前路茫茫,竟不知该往何处去——仿佛这人生,也如那股市一般,转眼便跌得一败涂地,连翻身的力气,都有些匮乏了。
二零零六年,意大利人将那尊铜铸的大力神杯抱在怀里的次日,我立在南京站的风里,与相交数月的女子挥了挥手。无半分戚戚,亦无片缕惜别,只觉风裹着尘沙,扑在脸上,凉得有些茫然。列车的鸣笛声扯得老长,像极了困兽的呜咽,我扒着车窗,看窗外的景物一帧帧向后退,如同我那尚未铺展便已被钉死的前路——家里捎来话,叫我回电白报到,穿上那身素色的教师衣裳,从此困在一方讲台前。这份“前程”,于我而言,无半分欢喜,只余满心的混沌,像蒙了层灰的镜子,照不见半点亮光。
老辈人的心思,大抵是刻在骨头上的:族要立住脚,总得有人往外闯,挣一份前程;也总得有人守着老宅,续一份烟火。父亲早已在外头奔波,留了叔叔在家侍奉祖父母,他怕我在外头成了无依无凭的“无鼻牛”,东碰西撞,终是一场空,便替我选了师范的路子。我那时竟也应得爽快,只因听几位师兄嚼舌根,说师范里头,尤其文科,一个班里几十号人,男子不过三五个,端的是“肉少狼多”,便是一月换一个女子相伴,待到毕业,也未必能轮遍。这般荒唐的念头,竟成了我当时欣然应下的由头。大学四年,兜里侥幸有几个闲钱,便也浑浑噩噩,算得“潇洒”了一场,如今想来,不过是少年人的虚妄罢了。
虽应了家里的安排,可前路于我,依旧是雾里看花,茫茫然辨不清方向。归了家,从教局报到到学校上岗,竟如提线木偶一般,被人牵着走,说不上情愿,也说不上不情愿,欢喜二字,更是无从谈起——仿佛这身子不是自己的,只是按着力道,做该做的事。
到校报到那日,教办的屋子里挤着十五个同来的人,我是最后一个被领走的。来接我的校长,浑身酒气熏人,双眼朦胧,似是还浸在醉意里,含糊问了几句我的来历,便摆了摆手:“搭我的摩托回校?”我摇头:“不必,不如我用小车送您?”他猛地睁了睁眼,错愕片刻,而后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:“刚当老师的,薪水薄得很,你那工钱,怕是不够给车加油。学校地址认得?你先去,我随后就到。”我应了声,便驱车先去了。
我该是镇上第一个开着小车去教书的新先生,自然引来了不少目光。有含着羡慕的,眼睛亮得像要沾点光;有揣着怀疑的,眉头皱着,猜我是来混日子的;还有等着看笑话的,嘴角挂着冷笑,盼着我摔个跟头。世人的心思,大抵是这般,见不得异于常人的,总要揣度几分,议论几句。
归了学校,没等多久,校长也晃悠悠来了,召了众老师开会,无非是把我这个“新丁”推出来,说几句场面话,便引我去看宿舍——竟是一间旧教室劈成两半,里头空荡荡的,只有前后两扇窗,和一扇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木门,风一吹,便“吱呀”作响,像在哭。这宿舍,我四年里竟未住过一宿,只摆了一张竹椅,闲时蜷在上面歇片刻,倒也清净。只是那份薪水,果然如校长所言,薄得可怜,当真不够给车加油,想来也是可笑。
八月三十一日的早会,迟来的课程表终是递到了我手上——五(二)班的语文,兼着班主任。散了会,校长便唤我:“你有车,去把书本作业本拉回来。”我应了,心里却没什么波澜。九月一日,第一堂课,我没发书本,只和三十几个孩子坐着说话,你一言,我一语,光阴竟也溜得快。第二堂课,依旧没发书,我在讲台上扯着自己那些荒唐的“风光事”,台下哄笑一片。这些不过是哄着孩子们欢喜,也哄着自己欢喜。先前有前辈告诫我,这班是全镇倒数第一,调皮捣蛋的多,还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是混江湖的,叫我当心些。我倒觉得,倒数第一也好,没什么指望,便也没什么压力。第三堂课,才慢悠悠把书本发下去。人生大抵是没什么意外的,期末考下来,依旧是倒数第一。只是这一学期,倒也清净,孩子们打架的少了,家长的投诉也稀了,大抵是我这般“不务正业”的先生,反倒合了他们的性子。
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学校这方寸之地,竟也不例外。二十三个老师,硬生生分成了几派:校长与出纳是一伙,攥着些细碎的权柄;主任又是一派,暗里较着劲;还有些官太太,仗着家里男人的名头,也自成一派——这学校离墟镇近,官太太也多。我呢,踩着钟点上课,无课便回了家,不攀附,不掺和,倒也成了独一份的“派系”。正因这般,那些校长里短的八卦,便总往我耳朵里钻,听得最多的,莫过于校长的那些风流韵事,荒唐得很。
在校长和主任眼里,我大抵是个来体验生活的公子哥,瞧不上,也懒得真管。那些官太太,却也把我当成公子哥,隔三差五便来做媒,拉着我见了两三个女子,我皆是落荒而逃——并非她们不堪,只是瞧着那般刻意的模样,只觉无趣。后来再有人来说媒,我一概回绝,倒也暗暗疑心,她们的审美,怕是被世俗磨得走了样。我素来只在上课时分现身,这般“鹤立鸡群”,自然引来了不少关注。许是校长瞧我不顺眼,许是有人在背后嚼舌根,每次开会,总免不了点我的名,说几句批评的话。我听着,只当是耳旁风,依旧我行我素——横竖我没害人,也没误事,何苦要顺着旁人的心思活?
次年,她来了。她这一来,倒把我原本死水般的日子,搅得浑了。她是我大一的第一个女子,也是大学四年里,相伴最久的一个。先前平静分手,闲来无事,只在QQ上聊几句,吐吐各自的苦水,谁知吐着吐着,竟出了岔子。人呐,大抵是逃不过“犯贱”二字的。这傻丫头,竟悄无声息辞了职,不顾家里的反对,一路南下,说是来“讨债”——讨我当年的亏欠。家里人自始至终,都盼着我找个有单位的女子,安安稳稳过一辈子,可那些有单位、模样稍周正些的,偏生瞧不上我们这些穷教师。她能让我那素来反对的父母松口,大抵是因祖父生病时,她守在床前,悉心照料了两个月,这份情分,老辈人是认的。旁人皆是工作爱情双丰收,我却因她的到来,过得捉襟见肘——既已工作,再向家里要钱,总觉难堪,又添上那时爱赌的毛病,日子愈发窘迫,外出闯荡的念头,也便在心里生了根。
二零零七年,我成了亲。父亲竟破天荒从他的公司里,分了些股份和分红给我,说是补偿我留下来守着家里的辛苦。他还唤来两个弟弟,叮嘱道:“日后无论你们谁接手公司,谁另起炉灶,都要分他一份股份分红。我老了,总要回乡下养老,到时候,便靠他照料我和你母亲。”弟弟们应得爽快,想来也是默认了这份安排——我守着家,他们在外闯,各取所需罢了。
二零零八年,倒是不平常的一年。薪水涨到了八百多块,算得一份微末的平静;可股市里,牛市转眼变熊市,五千二百多点直直跌到一千八百多点,先前赚的那些钱,亏得干干净净,反倒欠下二十几万的外债。偏生这年,大儿子也来了,哭声震天,却驱不散我心头的愁云。那时的我,愁绪比胡须还长,望着屋顶的梁,只觉前路茫茫,竟不知该往何处去——仿佛这人生,也如那股市一般,转眼便跌得一败涂地,连翻身的力气,都有些匮乏了。